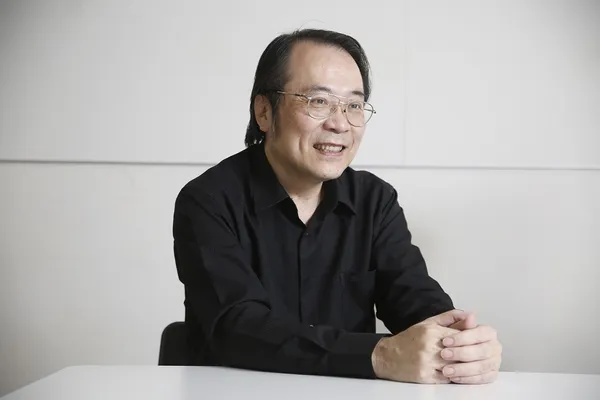當AI改寫世界,台灣下一步怎麼走?Google台灣區前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從硬體、軟體到軟硬整合、企業合作的角度,定義台灣在AI時代的版圖定位。
2024年8月,Google前董事長施密特在美國史丹佛大學演講時,屢次提及台灣,尤其是台積電和台灣的軟體。他說:「Amazing hardware, software is terrible.」(硬體很棒,但軟體很差。)
我在這位老長官拜訪台北時也曾聊過此議題,這是台灣產業長期以來的挑戰,與台灣硬體產業以代工為主的特性有關。要是硬體能成功建立品牌,如同宏達電(HTC)、華碩、宏碁過去達到的成就,企業勢必會投入大量資源去開發、整合專屬軟體,自然帶動軟體實力的提升。然而,台灣產業以代工居多,具世界影響力的硬體品牌更是屈指可數,導致軟體通常由軟體商自行開發,使得台灣軟體在產業發展中很容易被忽視。
儘管2010年後,Appier、91APP、Gogolook等軟體業者紛紛冒出頭,並且陸續上市、取得佳績,成為倍受矚目的「台灣黑熊」,但目前台灣在世界舞台上最出名的軟體企業,仍是1988年成立的趨勢科技。
只著重硬體導致什麼問題?
硬體產業最痛苦之處,在於大量生產後,終究會走向低毛利。
台灣硬體的競爭優勢無庸置疑,我們有相當成熟的硬體供應鏈,也能以具競爭力的成本解決客戶問題,過去幾個新科技崛起的循環裡,我們的硬體都因此受惠。但是,只要進入到創新與應用的高峰期,成長的速度就會放緩。台灣資通訊產業能屹立不搖,部分原因是適時搭上科技趨勢的順風車,電腦走下坡後,又冒出智慧型手機,手機銷量下跌,再跑出AI伺服器,才能在AI時代的第一階段搶得先機、賺到錢。可是,硬體的需求終究會減緩,我們不能只當很會挖礦的鏟子,只賣GPU、AI伺服器,而應該去做應用、去挖礦,創造硬體以外的附加價值。
可惜地,目前一談到純軟體,我們就矮人一截。例如,我們沒有成功服務全球的應用程式、沒有大數據,因此無法發展雲端AI,尤其現在市場已經有Google、Microsoft這種純軟體服務商。軟體是贏者全拿的世界,誰掌握更多消費者,誰便勝出,台灣很少有規模化、國際化的軟體平台,這不是我們該搶占的市場。
我們的機會在「軟硬整合」,讓台灣的軟體服務能更好地搭載在硬體產品上,共同向外拓展市場。而且,必須是硬體整合軟體,因為硬體廠通常規模龐大,具備全球化的運營能力。他們更了解Nvidia、Apple、Google等科技巨頭的需求,能掌握軟體發展的脈絡與應用方向。
其實,全球最具指標性的GPS(全球定位系統)企業、台灣企業家高民環共同創辦的Garmin,便是結合硬體、軟體和服務,做出最佳軟硬整合的例證。
當年,Google地圖和智慧型手機問世後,立刻衝擊以車用GPS裝置為主力業務的Garmin。Google地圖的免費服務才上線兩天,下載量就比Garmin一年賣出的GPS還多,這讓Garmin的市值一度大跌87%,車用導航產品營收從占比七成,跌至不到二成。後來,Garmin重整步伐,發揮核心技術優勢,將GPS功能整合進運動、專業手錶,避開與智慧型手機大廠正面衝突,專攻定位精準、耐用、續航力強的垂直市場和高階戶外運動、專業應用領域,雖然無法在智慧手錶這個紅海戰場撼動Apple Watch的地位,卻因為避開「手機品牌思維」的同質化產品,深耕專業運動、健康管理與高階功能型手錶,銷售量長年位居市場前五。
邊緣AI撬開的新商機
錯過電腦、智慧型手機的浪潮後,現在機會再度降臨,邊緣AI又讓我們看到從雲到端、由硬到軟的希望。
什麼是邊緣AI?是將AI導入電腦、智慧型手機、GPS、智慧手錶、腳踏車等終端裝置上,而不是依賴遠端的雲端伺服器,從而提升產品附加價值。例如,將具備推理能力的生成式AI導入安控監視器,當你遺忘鑰匙放在哪時,它只要瀏覽你今天走過的軌跡,知道你有開門進屋,代表鑰匙一定在家裡,便能運用推理幫助你找到鑰匙。
對雲端業者來說,邊緣AI能分擔成本,假設今天有40億支手機都在使用Google,但它們都裝載邊緣AI的晶片,Google就能省掉40億支手機的運算成本。
邊緣AI還能滿足日漸重要的資安需求。手機中的AI助理可以只存在於手機中,個資不用送回雲端運算,用戶甚至能要求AI助理刪除特定資料。尤其美中對抗未歇,更需要注重資安,加上去紅供應鏈的情勢,都有利於台灣投入。
事實上,類似邊緣AI的機會,在電腦時代已經為我們演繹過一次了。
回憶一下,1985至1990年代,我們最初使用電腦是不是不用花錢買軟體?全都用被稱為「大補帖」的盜版軟體。追根究柢,最終消費者會購買硬體產品,往往是看中捆綁、內建的軟體服務,軟體是附加在硬體裡頭活下來的。現在就像當初一樣,消費者很少人直接付錢給AI,日後的AI服務會加在哪裡?加在iPhone這類熱銷產品裡頭,最後才會活下來。
一旦AI走到終端裝置階段,我們的機會就來了。因為,台灣是全世界工業電腦的大國,能將很多應用軟體加在我們生產的各種硬體上。工業電腦、機械手臂等硬體本來多數沒有腦袋,只要加上AI應用,有辨識、生成能力,它就有腦袋了,許多隱形冠軍都需要這種輔助技術。台灣產業可以善加利用開源資源,為硬體裝上腦袋,這會是我們的天下。
只要跟著終端裝置出海、打市場,像是捷安特(Giant)的自行車賣到全世界,讓每個消費者使用的裝置裡裝有我們的純軟體AI服務,不僅能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,也能提高銷售價格。
那麼,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模式,加強從雲到端、由硬到軟的整合?
老創、新創的超級整合
目前,台灣的問題是做軟體的人大多沒有能力、動機去了解硬體。投入軟體創業只需要會寫程式即可,但要創業家改去製造智慧路燈,除非他家學淵源,家族本來就是從事相關行業,否則沒有辦法切入。
一方面,我們可以鼓勵學生就學時嘗試更多課外內容,實務上也要打造平台、舉辦更多交流活動,促成「老創+新創」的組合。
再者,老創——數十年前起家的傳統產業,在台灣甚至國際上都占有一定的江湖地位,現今正面臨AI時代的轉型問題;新創則是擁有網路、AI能力的團隊,但缺乏算力、數據和商業情境。
有趣的是,台灣老創(一代)、新創(二代)的差異,正好是由網路的興起來劃分,形成獨特的「網路代溝」。不同於美國早在1970年代便開始發展網路,2000年前後,全球化浪潮席捲台灣,父執輩開始將重心轉向中國,主力發展製造業,經營上採取壓低成本以實現規模化的模式;管理思維則傾向集權、層級分別。與此同時,當時約20歲的年輕世代,因為看見充滿機會的網路而投入其中,雖然歷經挑戰,許多人看似被網路泡沫「淹沒」,實則累積了寶貴經驗與潛力。
這些差異讓老創和新創之間,無形中產生了「網路」與「非網路」世代的思維衝突。前輩較不重視品牌、高毛利產品,後輩則忽略了前輩的規模化管理能力與全球營運經驗。台灣的一代做製造業,二代投入網路內容產業,剛好讓兩代創業家位處微笑曲線的兩端,遙遙相望。
但是,進入AI時代,當網路內容、製造業都需要用到AI時,老創和新創就有機會產生交集、激出火花了。因為,AI和百工百業都有關,而且愈強大的產業愈需要用AI,硬體產業不用AI、不用智慧製造,如何邁向永續?軟體產業沒有規模化也活不下去。半導體是這個時代最龐大的產業,客戶近在眼前,軟體業不去接近他們嗎?
我從Google退休後,花了五年在新創走了一圈,現在又在老創徘徊,擔任統一企業、達發科技、華碩電腦的獨立董事,以及中華電信的法人董事。我的期待,是拉近老創、新創和政府的連結,將微笑曲線的兩端拉在一起,做到超級整合(Super Integration)。
我相信在AI時代,台灣循著老創帶新創的路徑,從雲到端、由硬到軟,很有機會。例如,現在的聯發科不只是一家晶片公司,也是一家AI公司,成為台灣AI的燈塔。中國AI發展得如火如荼,聯發科正是中國AI晶片的重要供應商,因此他們擁有全台最多的AI知識和經驗,看得到應用在哪,能借力AI做晶片設計。儘管,聯發科不缺資金,近來還是有許多創投、科技大老紛紛投資聯發科創投,期盼與之合作,就是因為他們看得見應用在何處。
研華的工業電腦則是另一個好例子。如今,研華的工業電腦不再只是「有手有腳」的工具,反而跳脫傳統製造的框架,將AI模型透過開源軟體整合進系統,將路燈變成「有腦袋」的智慧設備。一根路燈裝上AI可以變聰明,但路燈還是要面對風吹雨淋,而研華的工業電腦能提供耐用且穩定的解決方案,確保AI在戶外環境運作得宜,這正是台灣的優勢所在。
機會已經來臨,只要老創、新創敞開心胸,從雲到端、由硬到軟,攜手共舞,將能重新定義台灣在全球科技版圖上的地位。
本文授權轉載自《台灣AI大未來》
作者:簡立峰
出版日期:2025/09/09